鄭台祥
Visible/ Invisible(可見/不可見) 是人們閱讀地景時經常會遇到的一組關鍵字。乍看之下它一刀兩斷,卻也帶點藕斷絲連的味道。你很難不把這一命題持續看下去、想下去、延伸下去,如同挖掘礦脈。在哲學界,法國現象學家梅洛龐帝拿它來當作書名; 在景觀設計界,美國設計師Reed Hilderbrand也拿它來當作書名。是了,可見/不可見,這一組充滿張力的關鍵字,橫跨了哲學與地景,也為「觀看」這個人類最本質的行為,劃定了一道若有似無的認識論界線。彷彿一道羽毛緩緩從天而降,輕飄飄地,不偏不倚落在兩者之間。
這本名為可見/不可見的作品集,以攝影集的形式呈現。透過鏡頭語言,斑駁樹影時而靜默,時而搖曳生姿,水面輕風拂過,激起陣陣漣漪,像是轉瞬即逝的木漏光痕,幽玄侘寂一應俱全。彷彿隔空呼應了日本禪修大師枡野俊明筆下的「看不見的設計」。一片禪意初心之外,還夾雜著一絲Peter Walker口中「第三波現代主義」的極簡氛圍。只是場景換到了美國,細節尺度也難免跟著大手大腳了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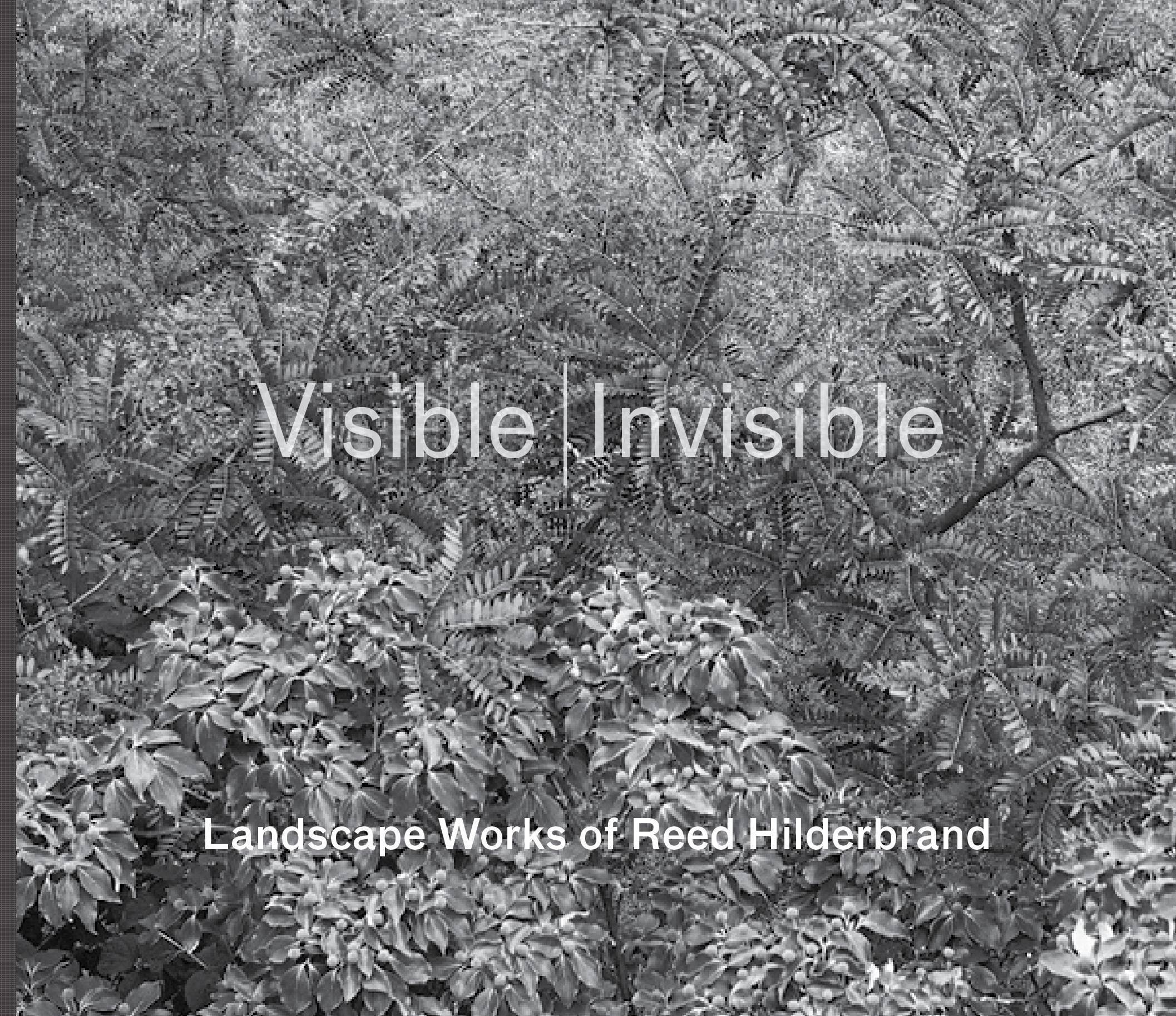
一間位在麻州劍橋,學術根底深厚的老牌景觀設計公司,選擇用「攝影集」這一媒介來呈現作品,或許算不上前衛,但多少也算是匠心獨具的。然而,這匠心獨具的背後,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風險。尤其身處在一個圖像訊息爆炸、滿溢的社群媒體年代,人們對於「攝影」這一高度選擇性、遮蔽性的視覺媒介,或許打從心底都懷抱著些許警惕與不信任。
這一警惕、不信任、乃至於敵意,究其原因,恐怕很大一部分源自於這所謂「選擇性」與「遮蔽性」,在買賣交易主導的商業語境下,經常涉及「廣告不實」的嫌疑吧? 人們經常有一種預期心理,那就是會下意識地把照片當成一種類似信物般的呈堂證供(豈不聞「有圖有真相?」),尋幽訪勝之餘,會不斷比對現場與照片之間的差異。若是誤差尚在可忍受的範圍內,心中嘀咕幾句也就罷了。但偶爾也會出現差異過大導致難以忍受的情況。像是早年的泡麵包裝,撕開豐盛精美的外盒,才發現裏頭一片肉也沒有。

說起來,我其實無意探討上述所謂「選擇性」、「遮蔽性」等等,在當代視覺文化的脈絡下是否有「廣告不實」的疑慮,更無意強弩之末般的鑽入其衍生種種諸如「真實vs.虛構」等邏輯啦、道德啦…之類教條式的、極易流於泛論的題目。相較之下,我更關注的還是作品集本身的名稱: 可見/不可見。像是一則言簡意賅的宣言,它坦然、甚至欣然接受了上述諸多疑慮,包含了攝影被誤解、曲解的種種可能性,目的就是為了告訴人們: 選擇性的遮蔽,本來就是地景成立的大前提。
選擇性的觀看,同時也是選擇性不看: 人們經常掛在嘴邊,說要「培養觀看的能力」云云,卻很少說培養「視而不見」的能力。關於這一點,專業攝影家往往比誰都清楚(近乎一種天性與本能)。對他們來說,選擇性的遮蔽,毋寧更像是日常工作的一部份: 透過鏡頭觀看、取景,拍攝畫面構圖、聚焦、後製階段編輯、裁剪…。同時,它也意味著大量的捨棄,每一次拍攝,快門一按下去,少說也上百張起跳。何況資料夾裡頭還存放著過往累積動輒數以萬計的影像庫存,你怎麼可能要一次全讓人看見呢?

因此,當我搜尋腦海中的資料夾,試圖挑選一個案例來描述這「可見/不可見」,首先浮出水面的,是多年前一次短暫走訪西麻州的克拉克藝術中心,庭院中那一大片水池,清風拂面,搖晃著水面倒映出那一抹伯克夏郡的群山淡影。
克拉克藝術中心(Clark Art Institute)靜靜坐落在西麻州風景如畫的山谷,緊鄰大學城威廉斯鎮,於2014年重新開幕。施工前後歷經12年,內容包含了基礎設施重建、舊館整修、增添新館等。Reed Hilderbrand負責戶外景觀設計,他們的主要任務之一,是將三棟不同時期、風格各異的建築物,分別是遊客及會議中心、美術館本館、研究中心給整合起來,當中最關鍵的角色,就是位於基地中央的大水池。
從地景的「績效」方面看來,該水池是整個園區水循環系統的核心。來自四面八方的雨水,透過地形、管線、鋪裝等等,被引流至此。水池底部的蓄水槽,回收的雨水經過過濾、消毒殺菌、清潔程序後,供館內廁所沖洗以及館外庭院灌溉等等使用,如此一來,據說每年可幫館方省下了超過百萬加侖的水源。事實上入園訪客從停好車的那一刻起,映入眼簾的便是亂中有序、順應地形起伏,具有海綿功能的生態草溝(圖四)。

儘管中央水池的責任如此重大,然而人們第一眼注意到的往往是它的簡潔造型: 輪廓清晰、線條分明,彷彿呼應了安藤忠雄設計的遊客中心。水池邊緣由預鑄混凝土版單元構成,塊石邊緣俐落地分隔草坪和水面,一切都精準的毫無懸念
,透露出日式匠人工藝的偏執,沒有一絲一毫模糊空間,當然也沒有許多台灣業主心心念念的所謂「安全至上」單細胞思維模式,凡水池不由分說必先加上一段護欄,以防止跌落。不到10公分的水深,究竟是要淹死誰?

然而,根據筆者不負責任的觀察(要說臆測也行),這個水池至少還隱藏了三個不那麼可見的特徵:
第一,水池的方位。它位於入口遊客中心南側,這一帶山谷地形夏日吹西南風,風吹拂過水池,蒸發的濕氣迎面而來,有助於遊客們第一時間降低體感溫度,喘口氣底定身心,炎炎夏日增添舒適涼感。此乃溫控調節方面之考量。(圖二)
第二,水池的造形。它乍看之下是方形,實際上水池由北向南分成三階段,逐步跌落(圖六)、寬度逐步遞減,整體形成一個下窄上寬的梯形(圖七)。這樣的手法,令人聯想到西歐幾何庭園常見的偽透視,視覺上強化了縱深,儘管效果並不顯著。此乃創造景深方面之考量。(圖三)
第三,水池的表情。平靜無波的時刻,通過水面的倒影,將周圍遠處的群巒疊翠納入場地,在室內與戶外創造出一個鏡像的空間。倒映天空、建築與周圍青綠山脈,有如一道變動而不確定的展牆(圖八圖九)。此乃水平借景方面之考量。





在日式庭園設計的傳統裡,無論是平安時期的寢殿式、書院式、乃至江戶時期的迴游式大名庭園,水池經常被視為一種整合建築與地景的媒介: 透過水面倒影,聯繫起室內與戶外,為觀者創造出一個鏡像的空間,一個雙重世界。水池表面看似平靜無波,實則在黑暗地底無止盡循環往復。透過這一面鏡子,也引發了地景設計裡種種關於可見/不可見的想像臆測。它不僅是鏡花水月式的,也是關於功能的、績效的、乃至於材料、構築、工法等各方面的實務考量。
談論地景設計裡的可見/不可見,其實也是在談論表層與底層; 談論地景的表層與底層,其實也是在談論可見/不可見。回頭想想Reed Hilderbrand的作品集標題,水池鏡面這一道若有似無的界線,是否暗示了「表裡地景」二義性、甚至多義性的共存? 當中的一槓,像是落在水面的羽毛,激起陣陣漣漪,向外擴散: 它頂多只是分隔,絕非對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