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台祥
“「幽玄」,就是「深藏內部的餘韻」,就是「想像看不見的事物」…這是一種不全部展現,隱身於後的典雅……庭園創造的重點在於看不見的部分,而非能夠立刻看見的部分,旨在提供觀者於自己內心中描繪創造…”
--枡野俊明《看不見的設計》
 有很長一段時間,如果您仍保有逛書店的習慣(無論實體或線上),或許不難注意到,有關「心靈勵志」、「人生體悟」這一類型的書籍,始終常踞暢銷排行榜前幾名的位置。而在這之中,有好幾本都出自於一位日本禪學大師之手: 他,就是枡野俊明。著有《你真的不必討好所有人》、《別對每件事都有反應》、《別動不動就自責》…等等,一系列耳熟能詳的散文小品。內容老少咸宜,包括了像是「早起喝一杯溫開水,避免內臟受寒」等的居家保健常識。不雞湯、不說教,隨手翻翻,倒也頗符合現代人只看標題的閱讀模式。
有很長一段時間,如果您仍保有逛書店的習慣(無論實體或線上),或許不難注意到,有關「心靈勵志」、「人生體悟」這一類型的書籍,始終常踞暢銷排行榜前幾名的位置。而在這之中,有好幾本都出自於一位日本禪學大師之手: 他,就是枡野俊明。著有《你真的不必討好所有人》、《別對每件事都有反應》、《別動不動就自責》…等等,一系列耳熟能詳的散文小品。內容老少咸宜,包括了像是「早起喝一杯溫開水,避免內臟受寒」等的居家保健常識。不雞湯、不說教,隨手翻翻,倒也頗符合現代人只看標題的閱讀模式。
枡野俊明生於1953年的橫濱,身兼寺廟住持、暢銷作家、美術大學教授等多重身分,同時也是一位頗負盛名的景觀設計師。他在橫濱的自家寺院擁有工作室,專門為神社、飯店、住宅等設計日式禪風庭園。他擅長將禪風精神高端化、庭園精品化,推廣至全世界。台灣最近完工的項目則位在高雄的亞洲新灣區,中華路上的一處頂級豪宅。
景觀設計師跨界寫作出版,以斜槓之姿賺進大筆財富,日本社會歷代不乏其人(另一例是昭和年間的公園設計之父本多靜六,據「我的財產告白」其一生積累數十億日圓資產)。事實上,禪宗僧侶中世以來作為知識分子代表,與社會緊密互動,除了青燈古佛下潛心修行之外,也積極參與學校講課、著述出版、企業經營…乃至媒體網紅等事務,亦不諱言為寺廟及個人積累大量之財富。另一方面,僧人古來奉行「農禪合一」、「勞動即修行」等「世俗不離道」的思想,日常生活業作如插花、泡茶、繪畫、造園等,無一不是道場,技藝發揮至極致,也就成為各領域之專精達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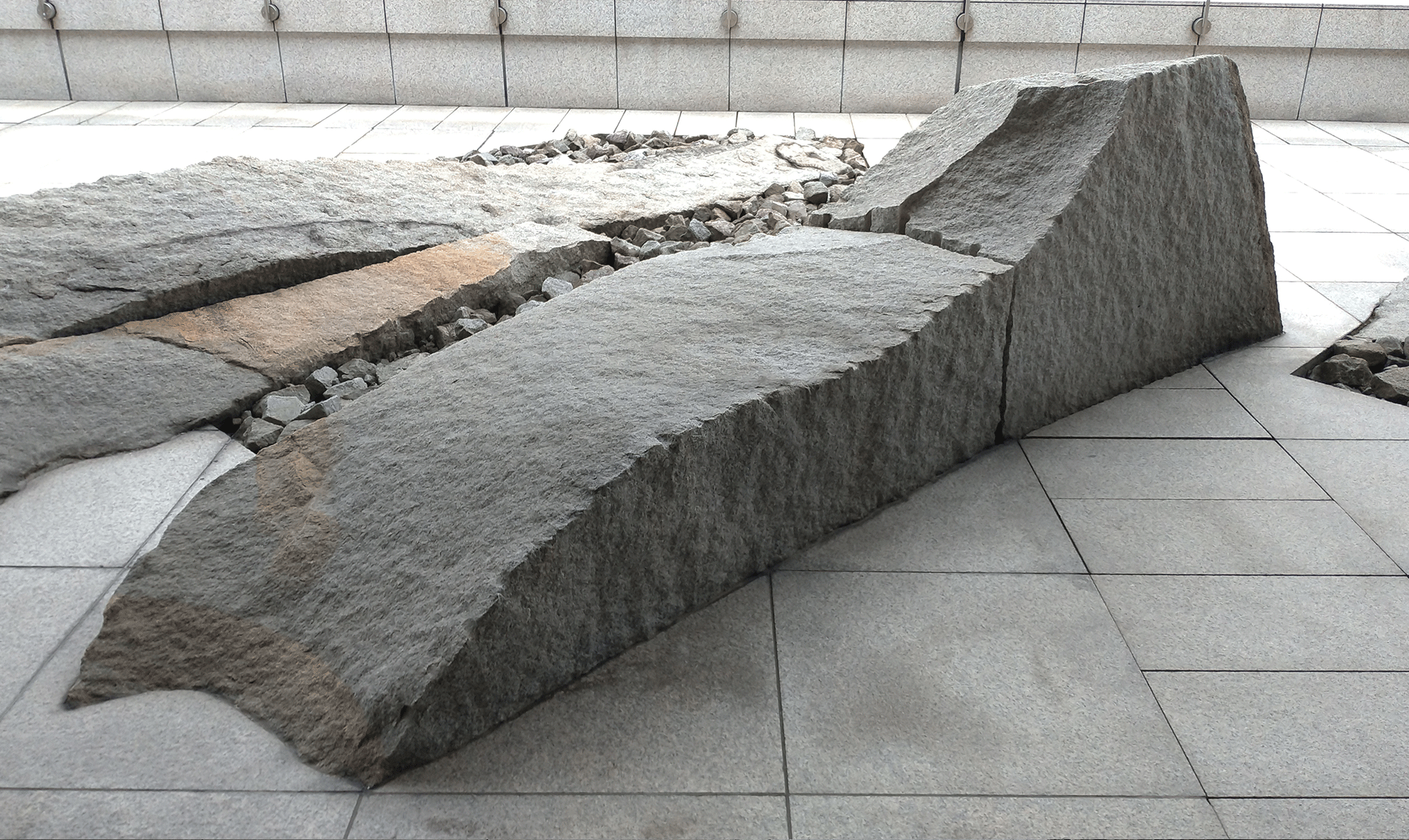 回到《看不見的設計》一書,書中出現的「幽玄」等字眼(其他包括了像是「枯高」啦、「留白」啦、「脫俗」啦…等等),你我應該都不會太陌生。然而,在這些耳熟能詳的字眼背後,往往隱藏著某些第一眼不那麼容易察覺的潛規則。其中之一就是它龐大的商機。比方說,作者既身為現代日式禪風的全球品牌代言人,如何不令出版社賠錢、如何不令事務所關門、如何不令石材工人失業、如何以寥寥數語支撐起整個造園設計、營造、材料、營銷、市場端的產業鏈。事關天下蒼生,因此它必須說的通俗而直白、老嫗能解,方能在最短時間內取得最大公約數,以符合世人心目中既定的日式美學印象,也才能順利取得歐美、中東、中國等海外尖字塔頂端客戶的合約訂單等等。
回到《看不見的設計》一書,書中出現的「幽玄」等字眼(其他包括了像是「枯高」啦、「留白」啦、「脫俗」啦…等等),你我應該都不會太陌生。然而,在這些耳熟能詳的字眼背後,往往隱藏著某些第一眼不那麼容易察覺的潛規則。其中之一就是它龐大的商機。比方說,作者既身為現代日式禪風的全球品牌代言人,如何不令出版社賠錢、如何不令事務所關門、如何不令石材工人失業、如何以寥寥數語支撐起整個造園設計、營造、材料、營銷、市場端的產業鏈。事關天下蒼生,因此它必須說的通俗而直白、老嫗能解,方能在最短時間內取得最大公約數,以符合世人心目中既定的日式美學印象,也才能順利取得歐美、中東、中國等海外尖字塔頂端客戶的合約訂單等等。
以今天的台灣為例,每年訪日人數多如過江之鯽,你當然不必是哈日成癮的建築愛好者,才有資格談論上述的日式美學。何況臉書上各式旅日建築達人、建築哲人、建築大叔、建築女子乃至都市偵探等主打美感京都怪獸大阪旅遊團進團出每日貼文到點打卡。當然也吸引了許多像我一樣,成天把「幽玄、物哀、侘寂」等掛在嘴邊,似懂非懂、一知半解又愛吹噓的初學者。 言多必失。人們選擇沉默,經常只是為了避免暴露短處、害怕被打臉、或在眾目睽睽相互監視的臉書語境裡淪為笑柄等等。換句話說,是為了自保,並非真有什麼了不起的高見。儘管這沉默卻常給人一種莫測高深的印象(或錯覺)。
言多必失。人們選擇沉默,經常只是為了避免暴露短處、害怕被打臉、或在眾目睽睽相互監視的臉書語境裡淪為笑柄等等。換句話說,是為了自保,並非真有什麼了不起的高見。儘管這沉默卻常給人一種莫測高深的印象(或錯覺)。
說起來,「幽玄」之所以顯得莫測高深,會不會也是因為它表面上看似沉默的特質? 按照枡野大師的說法,幽玄意味著透過「遮蔽、留白、削減」,來想像事物「深藏內部的餘韻」,來指向「不可言說」的部分: 只意會、不言傳、不立文字…禪宗公案一般。你該如何用有限語言(或是拙劣文字),來傳達出無窮意境呢? 想想老子說的話吧。「道,可道,非常道」,老子認為能說出口的道就不是道了。他不是在否定「道」,而是在否定「說」。
近年來,不乏許多西方好事者,試圖從比較文化論的視角來探討上述日式美學的本質,細細分析、表列區隔。這固然不失為一種透過比較來發現事物差異的手法。然而,在凡事皆須分析、極盡所能描述、皆充滿理由的實證態度之下,也給人不無一絲徒勞的倦怠感。想想老子說的話吧。能夠說出口的道,還算是道嗎?
 寫到這裡,我回想起了幾年前的那一次東京之旅。參觀了位在青山一丁目的日本加拿大使館庭院,也是枡野俊明早期的代表作(1991年完工)。直到最近,這個案例才又浮上腦海,或許可以用來說一說這所謂「幽玄」的奧義吧! 該使館位於都心的高檔地段,往東邊走幾步就是虎屋羊羹赤坂總店,往西邊走幾步就是神宮外苑銀杏並木。庭院對外開放,進了使館大門後填寫表格出示證件,經過基本安檢程序之後,搭上一道長長電梯,就來到位於四樓的庭院。
寫到這裡,我回想起了幾年前的那一次東京之旅。參觀了位在青山一丁目的日本加拿大使館庭院,也是枡野俊明早期的代表作(1991年完工)。直到最近,這個案例才又浮上腦海,或許可以用來說一說這所謂「幽玄」的奧義吧! 該使館位於都心的高檔地段,往東邊走幾步就是虎屋羊羹赤坂總店,往西邊走幾步就是神宮外苑銀杏並木。庭院對外開放,進了使館大門後填寫表格出示證件,經過基本安檢程序之後,搭上一道長長電梯,就來到位於四樓的庭院。
庭院呈ㄈ字形,三面包裹住大使館四樓的建築本體。從入口處往赤坂離宮的方向望去,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片高低錯落、參差不齊的塊石群組,連同挑空的長長屋簷,指向離宮的綿延樹海。每一塊石頭以斜向45度角排列,有些表面尚留有開採的鑿痕(矢穴),與地坪整磚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些造型粗曠的塊石,據說是設計意匠的表達,為了重現加拿大本土雄偉的冰川地貌。庭園盡頭有三塊金字塔的造型破土而出,旁邊則是一尊意味不明的雕塑。它的形體令人聯想到加拿大原住民因紐特人(Inuit)的傳統疊石。但左看右看,也像是一座石燈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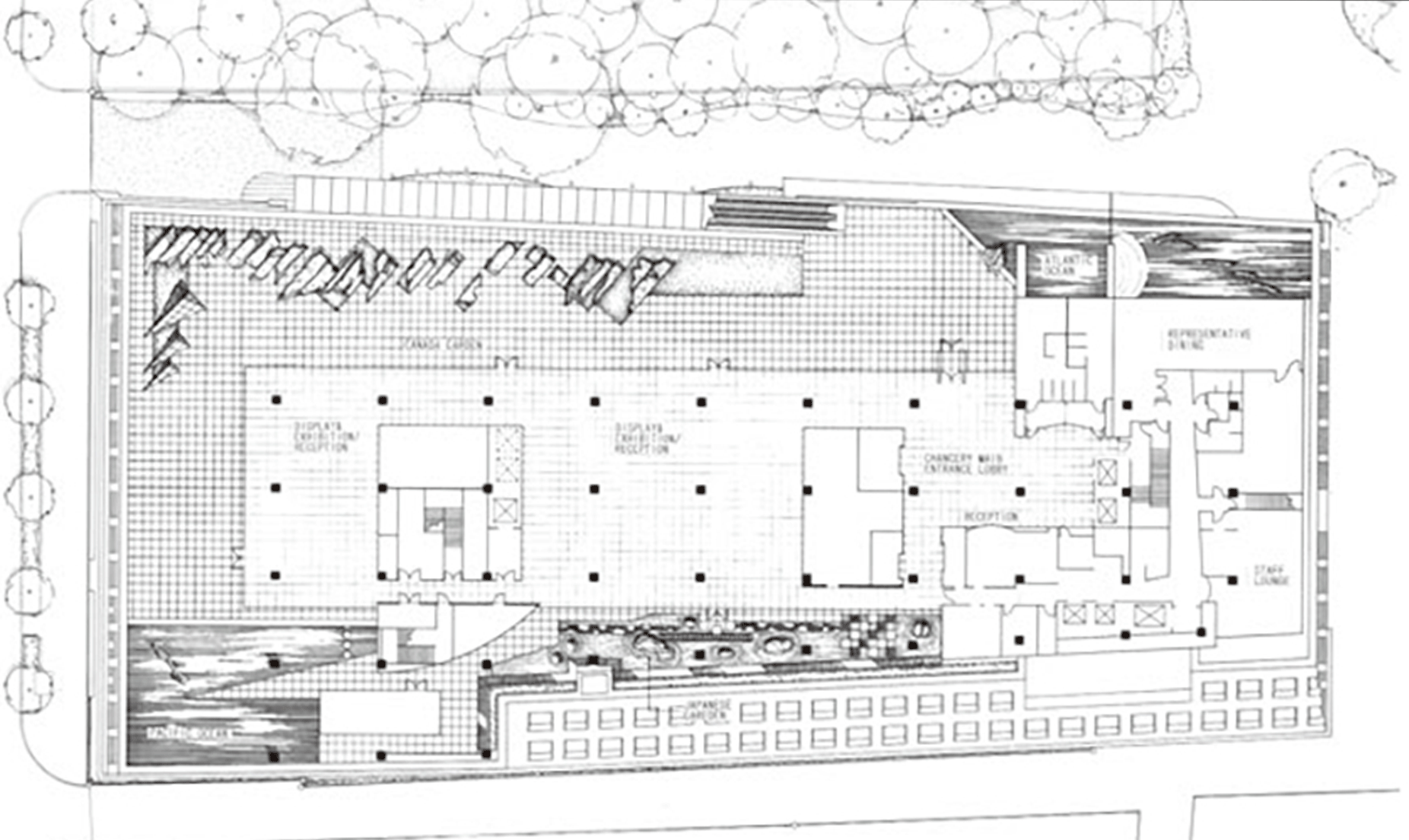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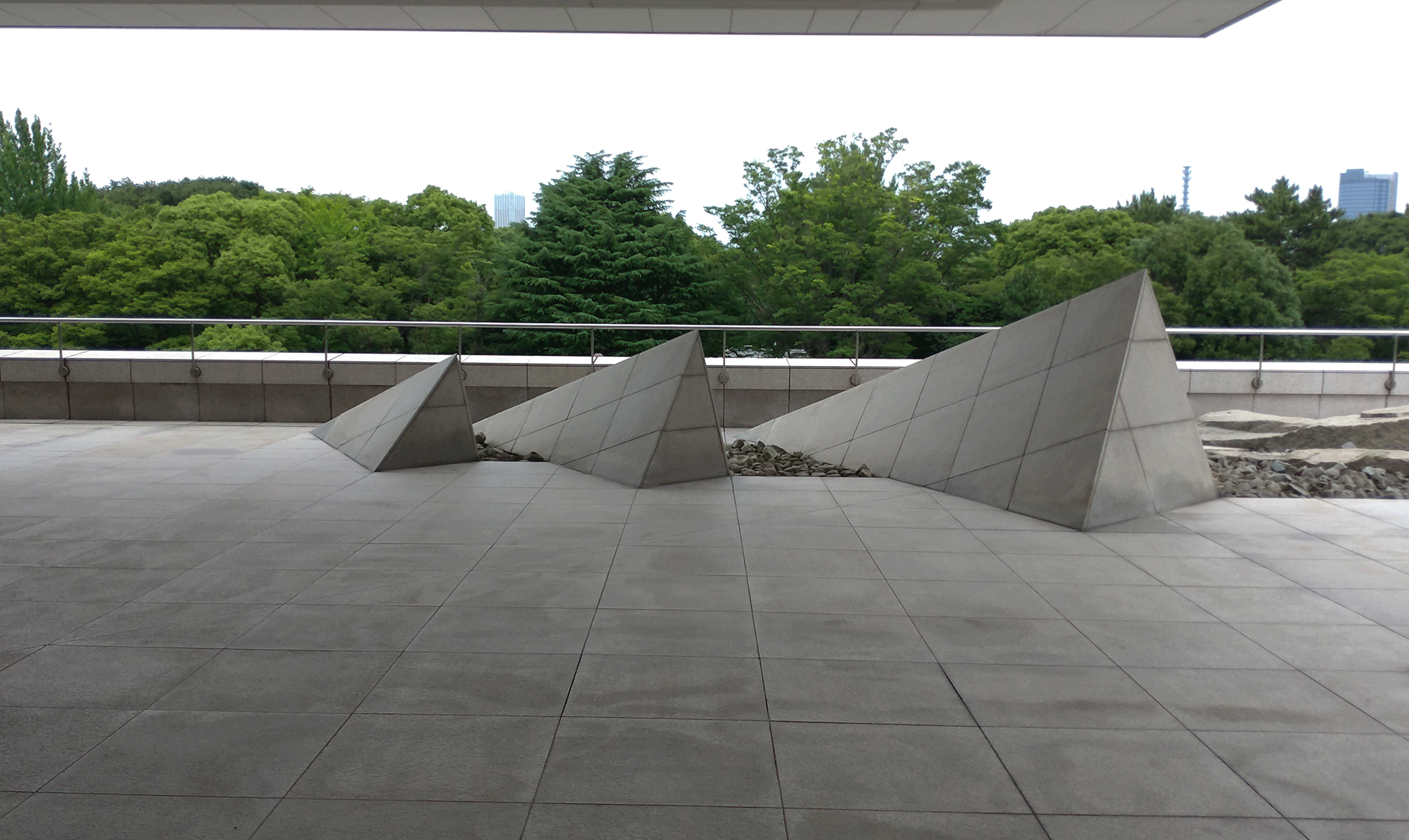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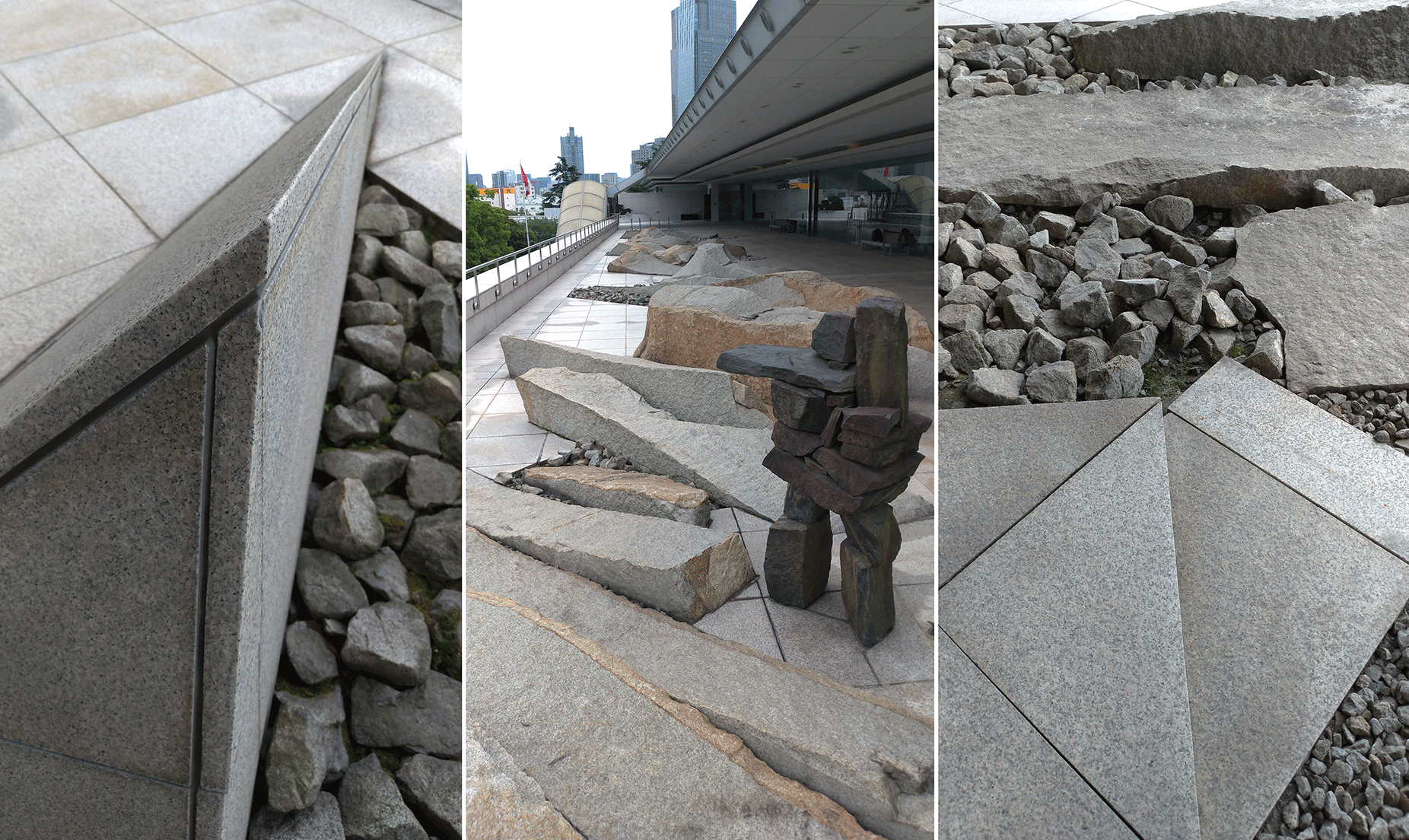 這ㄈ字形的參觀動線,據說靈感來自於一張世界地圖。電梯入口處的水池象徵大西洋: 由此啟航,首先經過塊石造景(象徵加拿大隆起的冰川地盾),一路延伸至端景(象徵北冰洋); 向左轉,進到位在西南角的另一座水池(象徵太平洋),再左轉,最終來到獨居幽暗一角的日式庭園。換句話說,作者試圖用這樣的手法,連結加拿大與日本兩地。咫尺天涯,將億萬里凝縮於方寸(這幾乎是日本庭園設計的傳統核心,縮小意識),勾勒出一幅大航海般的宏偉圖像。
這ㄈ字形的參觀動線,據說靈感來自於一張世界地圖。電梯入口處的水池象徵大西洋: 由此啟航,首先經過塊石造景(象徵加拿大隆起的冰川地盾),一路延伸至端景(象徵北冰洋); 向左轉,進到位在西南角的另一座水池(象徵太平洋),再左轉,最終來到獨居幽暗一角的日式庭園。換句話說,作者試圖用這樣的手法,連結加拿大與日本兩地。咫尺天涯,將億萬里凝縮於方寸(這幾乎是日本庭園設計的傳統核心,縮小意識),勾勒出一幅大航海般的宏偉圖像。
問題也就出在這一波三折的過程之中。這樣的動線規劃,儘管有戲劇化的效果,真正走訪時,才發現處處存在著斷層與遮蔽。最明顯的是,當你登上電梯,放眼望去,面對這一片來勢洶洶的造景,驚嘆之餘,也以為一切就到此為止了。沒想到越過一個轉角、兩個轉角…才發現深處還藏有一座日本庭園。這也太暗藏玄機了吧? 要不是後來看到平面圖,誰知道裏頭竟然還別有洞天呢?
也就是說,這個庭院採用了一群犬牙交錯的石頭組合,來製造驚喜,引導觀眾視線,卻在盡頭處來了個九十度大轉彎,一方面封閉了視野,也把東西給藏了起來: 曲徑通幽被直角一一給抹平,這恐怕是參觀者與設計者本人,都始料未及的吧? 另一方面,這座庭院打從一開始就呈現出最精彩的景色,開門見山放大絕,也因而確保了它的虎頭蛇尾: 遊人失去了興致,也就失去了向內探究的慾望。誰叫你把好東西一開始就讓人看光光了呢? 那麼,它到底跟「幽玄」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也沒什麼關係。可能就只是因為「錯過」所引發的種種後續效應罷了: 意識的斷層、不完整的體驗、事後諸葛的心態…眾多眉眉角角的毛邊,逐一積累、疊加、化為文字。參觀完這個庭院之後,我不確定自己是否離「幽玄」的理解更進一步,反倒覺得只是睜眼瞎子一般,盲人摸象。
那麼,它到底跟「幽玄」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也沒什麼關係。可能就只是因為「錯過」所引發的種種後續效應罷了: 意識的斷層、不完整的體驗、事後諸葛的心態…眾多眉眉角角的毛邊,逐一積累、疊加、化為文字。參觀完這個庭院之後,我不確定自己是否離「幽玄」的理解更進一步,反倒覺得只是睜眼瞎子一般,盲人摸象。
「庭園創造的重點在於看不見的部分,而非能夠立刻看見的部分,旨在提供觀者於自己內心中描繪創造…」這麼說起來,這「看不見」的部分,其實也無關設計者本身的意圖。想像啦、描繪啦、創造啦…說到底,人與地景的相遇,都只是盲龜浮木的偶然,是滿天星斗的交會。相見或不見,很可能就只是機緣巧合罷了,無序統治著一切。唯一確定的,那就是遮起來的,永遠比暴露的更讓人想一探究竟,不是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