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台祥
景觀設計師
美國麻省大學景觀建築碩士
如今還有多少景觀系學生讀《場所精神:邁向建築現象學》這本書? 黃皮封面、厚實沉甸,在許多大學建築系的圖書館裡,它依然以遠古神獸之姿,坐鎮在書櫃的角落,散發著一股莊嚴肅穆的氣息。這本書出版超過了 40 年,被譽為空間設計界探討現象學的經典,早在筆者求學時期,就已經是不少嚮往旅行與遠方的文青人手一本的必備讀物。雖然當時的我根本看不懂,至今也仍然努力地想讀懂它。
直到後來和一位前輩聊起這本書,才曉得,原來不只我,就連大學系上舉辦地景研習營的老師們也未必看得懂。這麼看來,這本書似乎符合了一條對「經典」的最經典定義:「人人都聽過,人人沒讀過(或沒讀懂)」。主要用途就是拿來引述、說嘴、掉書袋。這麼說並不帶一絲一毫嘲諷的意味,而是經典本身也有特定的、相當程度的門檻,也挑揀、過濾讀者,對讀者有所要求。以本書而言,那道門檻或許就是對「現象學」的基本理解。它硬生生的橫亙在讀者和書之間,如果一開始就不懂現象學的話,也別提什麼建築現象學、地景現象學了。

話說回來,本書 1979 年以義大利原文出版時,書名並無「現象學」一詞,是後來出英文版時才加上去的,無論是為了銷量或什麼的。總之,「建築現象學」一詞堂而皇之的出現了。
儘管書名冠冕堂皇,它卻未必是古往今來第一本把現象學概念納入空間設計界的開山之作(有任何一本書敢如此自稱嗎?)。書中大量引用了海德格、皮亞傑、格式塔學派的說法,試圖建立起一套對場地更整體的情境式觀察:光影、質感、氣氛……等難以言喻的場所特質。背後目的之一,則是為了批判二戰後歐美新市鎮計畫過度強調理性、機能、單一用途,導致人與場所分離、地方感流失的現象,也呼應了 1970-80 年代地域主義對早期現代性脈絡下普世、通用、無差別的挑戰,順勢重塑了人地關係的精神層面。如今批判現代主義、國際樣式的歷史文獻已多如過江之鯽,這本書依然占有一席之地。也多虧了它充滿儀式感的書名,當「場所精神」成為關鍵字,「地景現象學」的研究也一度被定義為「探討一個區域的自然地理特質如何成就了獨特的氣氛、場所與地方感」。

另一方面,《場所精神》一書的橫空出世,也讓在茫茫大海裡載浮載沉的地景設計師們發現了一片新大陸,在哲學、人文、心理等學科交岔路口找到了依歸: 地方感、自明性、回到事物本身……等關鍵字,隱約為似懂非懂的讀者們指點了一條路徑。於是我們這才發現,原來,條條大路通地景,而「現象學」正是其中一條。這條路我們可能天天都在走,卻從來不知道路牌上標誌著「現象學」三字。
因此,這當中勢必牽涉到一個理解態度的問題。建築、地景設計等科目,雖然傾向務實,然而回到理論的源頭,卻始終渴望哲學、心理學,向它們尋求借喻、支援與指引。身為一介「普通讀者」(吳爾芙語),如果不去動用到什麼「回到事物本身」、「從現象看本質」等過於浩瀚的詞彙,也不受困於自身針尖似的專業牢籠,更不以指點江山、好為人師的姿態來傳道、授業、攪和,而是把它當成一種世俗經驗下的常識,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來訴說,那該怎麼說呢?
很久以前,曾經在鍵盤鄉民的大本營批踢踢看板上瞄到一個標題。大意是說,如果把一個句子的主詞和受詞互換,以此範本來造句,會創造出怎樣的句子? 有人起了個頭,果不其然,是那句人人倒背如流的名言「當你凝視深淵,深淵也凝視著你。」接下來,便是每一樓接二連三的造樣造句。「不是你在看書,是書在看你」、「不是你穿衣服,是衣服穿你」、「不是你在數鈔票,是鈔票在數你」等等……目不暇給,令人莞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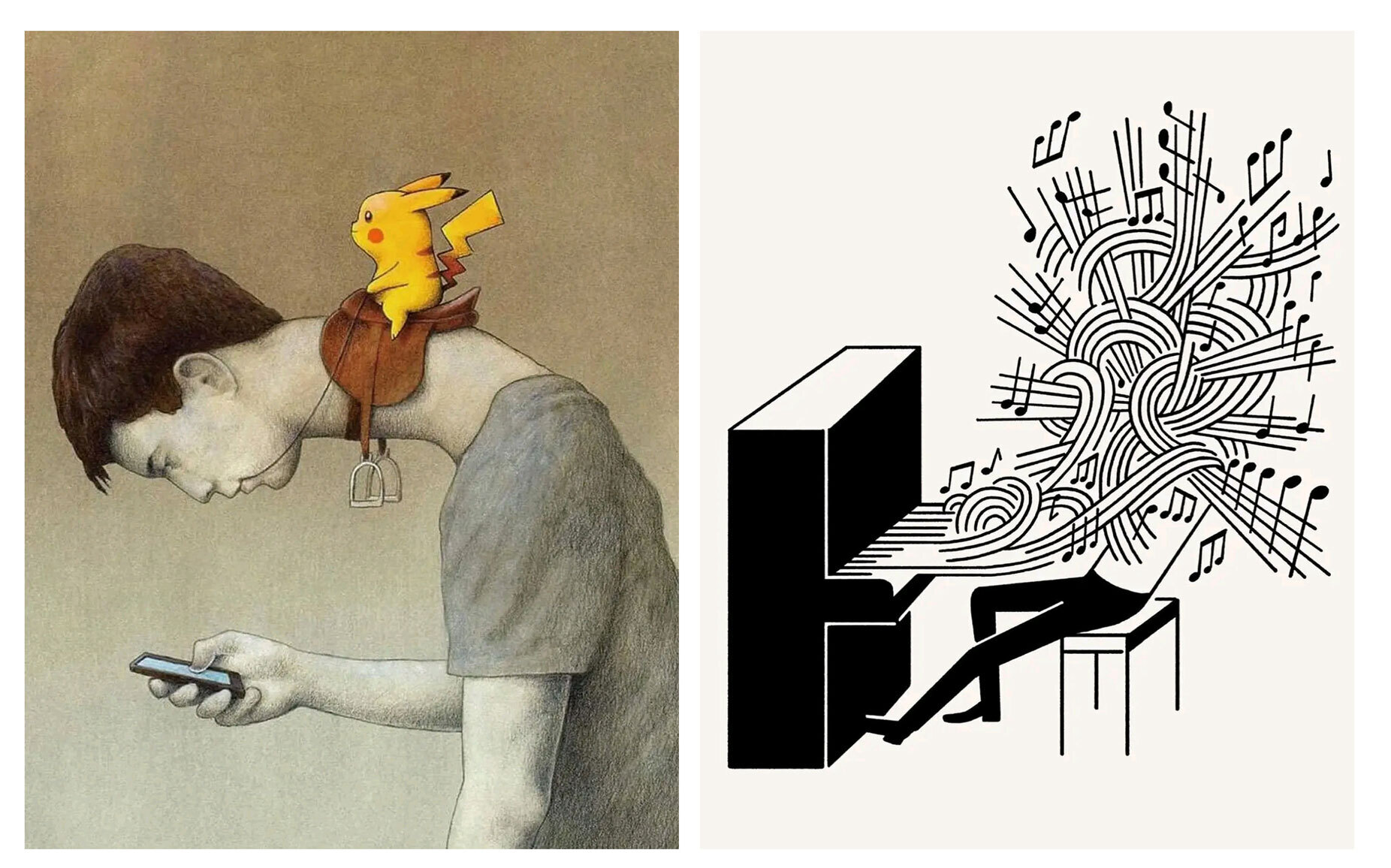
這當中固然不乏某種當今臉書世界常見的、集體嘲弄文青的酸冷趣味(批踢踢,你懂的),不登大雅之堂。之所以特意提出來,是因為我當時恰巧讀到了英國自然文學家羅伯.麥克法倫的《故道》(The Old ways)一書(此系列書籍近年來相當火熱,尤其出自以清冷蕭瑟為賣點的英倫島國)。說巧不巧,書中就出現了許多上述「主客對調」的句型。試舉數例如下:
1. 「每當他出門走向山,山便走入他心中」(p8)
2. 「人透過步行而探索內心,而我們行走其上的地景,則透過種種微妙的方式形塑了我們。」(p13)
3. 「我們很善於大聊自己如何創造地方,卻不太善於談論自己如何為地方所塑造。」(p43)
4. 「一旦走過了,古道便棲息於我們體內。」(p285)
除此之外,《心向群山》(Mountains of the Mind: a History of a Fascination)一書也出現以下段落:「我闖入野兔的路徑,正如野兔也闖入我的路徑。」
還有《大地之下》(Underland: A Deep Time Journey): 「只要你的心智更接近植物,我們就能用意義將你淹沒…你凝視(森林)這面網路,網路也開始凝視你…」(p122)

麥克法倫反覆使用類似「主客對調」的修辭法,來強化「地景與人心」之間的相互滲透。他書寫的對象是岩石、是浪花、是數億萬年深度時間下的地殼變動、板塊飄移,是天地玄黃宇宙洪荒中的海岸侵蝕、沙丘沉積。儘管隻字未提現象學、海德格、梅洛龐帝,但透過第一手的親身經歷,他旁敲側擊地為讀者詮釋了「身土不二」的另一種可能,也進一步令人聯想到關於身體現象學的另一組關鍵字:「可逆性」。
「可逆性」當然不只是主客對調然後照樣照句那麼簡單。現在回想起來,它有點像是「觀看下雨」這件事。下雨這件事好玩的地方在於,一方面它是現實的、集體的、雨露均霑的,另一方面卻也是隱喻的、個人的、參差不齊的。當連續幾天望著窗外的雨發呆,漸漸的,人很可能會分不清,究竟是哪邊在下雨了。(書寫這篇文章的當下,正逢颱風凱米來襲,足足看了三天雨)。
某位小說家以精闢的一句話總結這現象:「當意識以雨為中心打轉時,雨也以意識為中心打轉。」

也就是說,觀看下雨的同時,在意識和雨之間,究竟處在何種「接收-反應」的狀態呢?如果說,意識本身就有預知、甚至回頭強化外界刺激的能力,預感觸發記憶,記憶觸發預感……那麼,與其說它是一線性的因果關係,不如說更接近自體循環般的連鎖反應吧?既然身體,連同記憶一起,是「一切的邊境」,被「捕獲在世界的織理」之中,那麼早在我們對世界有所反應之前,世界就已經在那兒了。開放、共感、分秒疊合零時差……雨看似下在窗外,實則深埋在自身內部。這樣的解釋,不知道符不符合對「可逆性」一詞最起碼的理解?
類似的聯想,也見諸於巴謝拉(Gaston Bachelard)的《空間詩學》(The Poetic of Space):「我們居住在家屋之中,家屋也居住在我們體內,我們有意識建構房舍,房舍也無意識的建構我們。」當然,也別忘了梅洛龐帝推崇的大畫家塞尚(Paul Cézanne)的金句:「地景在我體內思考,我是它的意識。」

當「我」的身體成為地景的容器,透過「我」來思考、觀看,這意味著什麼? 古典光學意義下「第一人稱」的敘事觀點受到質疑,原有「理性客觀」的、單一固著的視角受到動搖。如同塞尚筆下目光游移、立體環繞的聖維多克山,透過畫家的手讓自己誕生。山的輪廓、形體不再是外部可見光反射的結果,而是宛如天燈一般,由內而外被渾沌的微光照亮,隨著筆墨深淺濃淡、色塊遠近明暗,一座山緩緩破繭而出。畫家與地景共同萌生……掙脫了繪畫主體與對象的束縛,「觀看」並不會因此讓我們遠離,成為地景的旁觀者。
這裡還是要提一下英戈爾,他不厭其煩的提醒我們,地景並不是事先預備好的實體,等待人類施為賦予意義,或是容納身體行動填補空虛。身體與地景兩者時時刻刻處於尋求互補的動態關係:並不是我們的行動讓土地發生了轉變,而是這轉變本身就包含了我們的行動在內。再一次,身土不二,完畢。

著陸(Landing)、以身為度、以足為度,走進土地、碰觸泥石樹草、觀察蟲魚鳥獸,感受光影變化……地景與人心的相互滲透,表現在設計、繪畫、書寫等,透過想像對方經驗、轉換彼此立場,深度介入、主客消融、成為它者…等方法,太多太多。
從拆解笛卡兒的「心物二元論」(Mind-body Dualism)開始,觀看之道、時間性、未完成、場所精神、可逆性……等等,這些看不懂的詞彙(大多出自歐陸白人男性)暫時盤據了我對「地景現象學」冰山一角的理解。儘管此刻它只能以一種東拉西扯、不著邊際的閒談方式說出來。往返在局部與整體之間,在瓦礫與星叢之間,我的感想是:「地景現象學」與其說是一門學科,會不會其實更趨向一種認識地景的心態呢?
刊出時間:2024 年 8 月 27 日
關鍵字:地景現象學、場所精神、可逆性、談天道地
